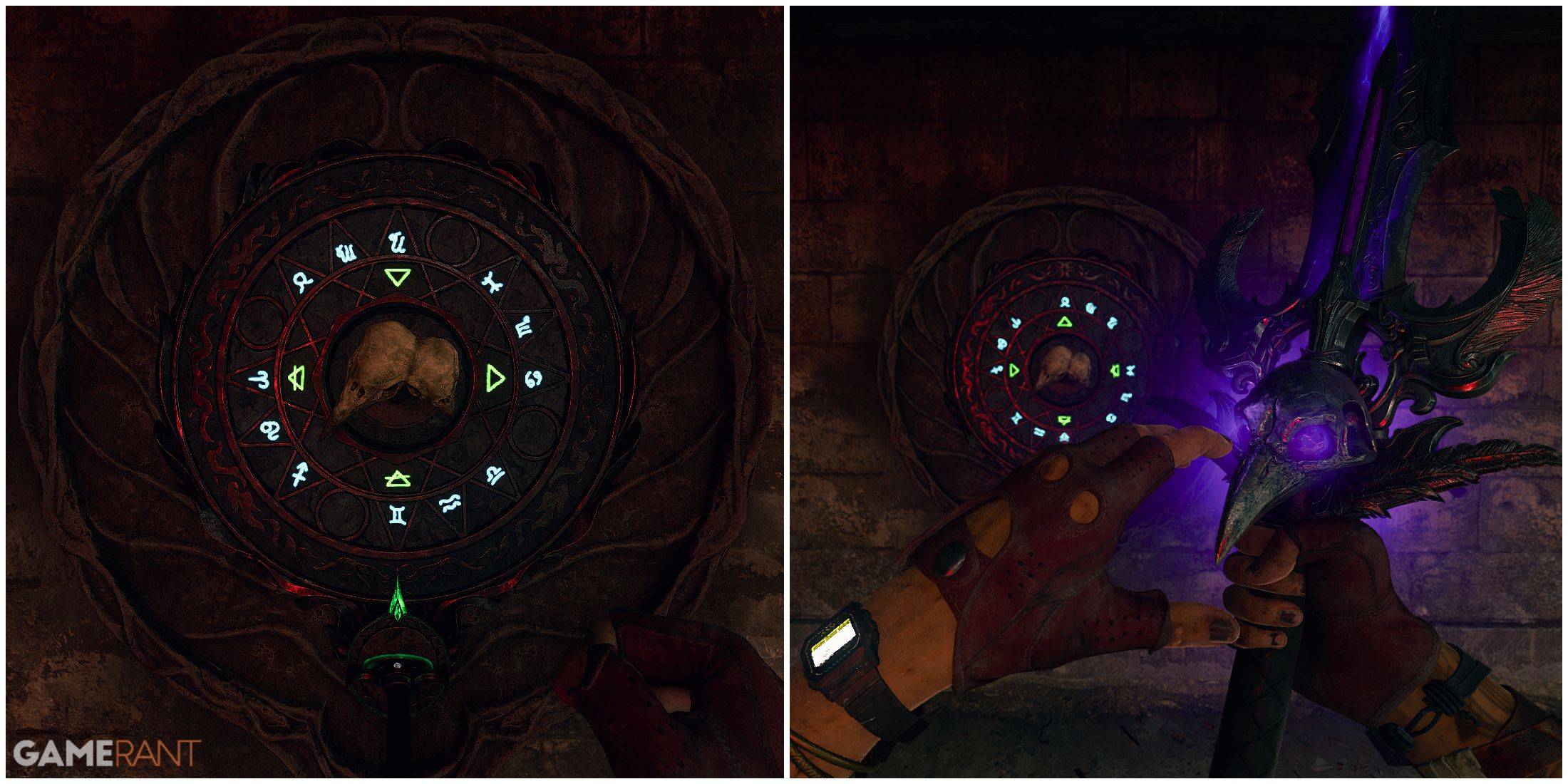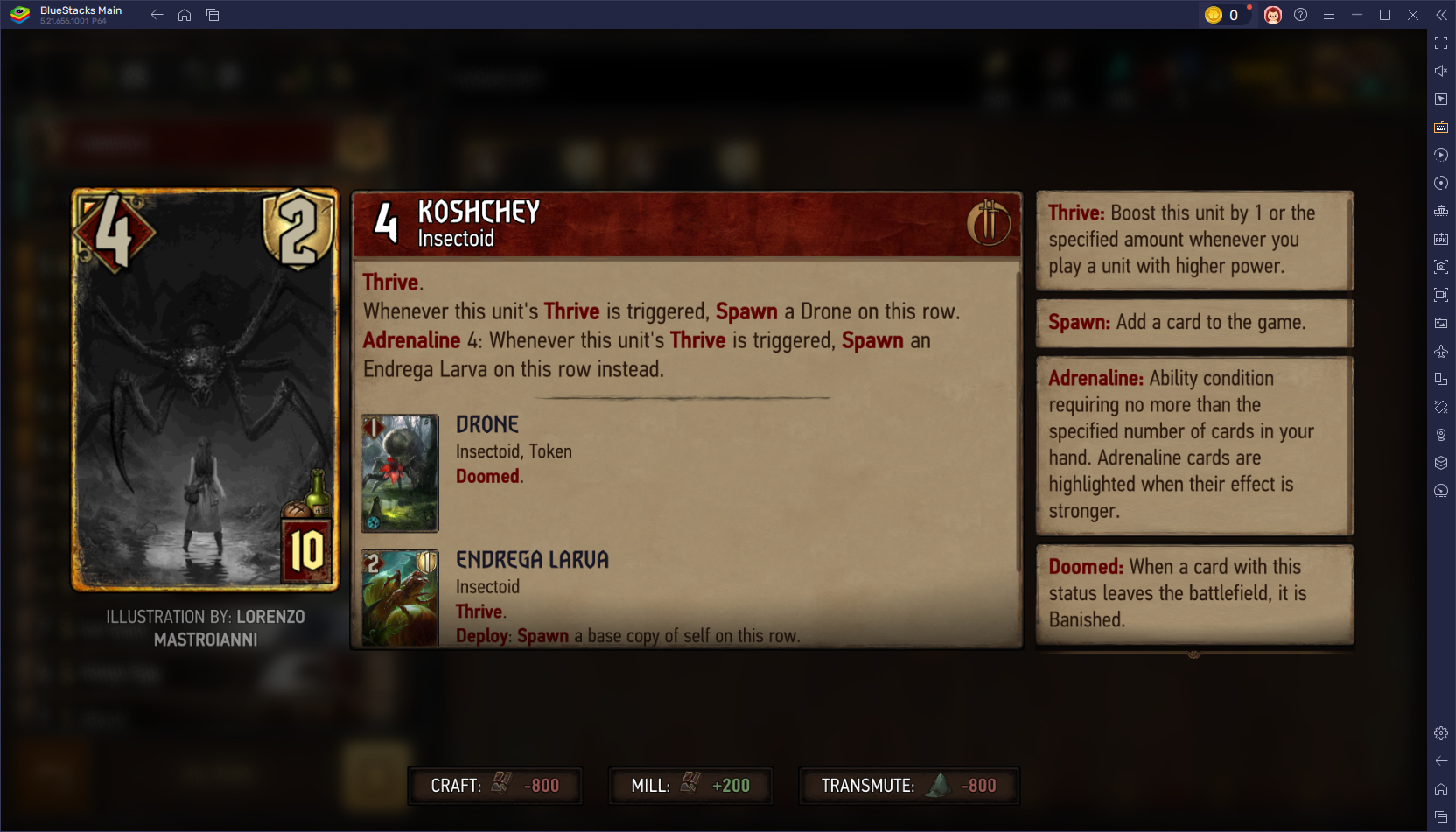「刺客教條 2 & 3」巔峰敘事之作
- By Samuel
- Sep 29,2025
《刺客教條》系列最令人難忘的時刻之一,發生在《刺客教條3》早期,當海瑟姆·肯威在新大陸集結他的團隊時。玩家起初以為這些都是同為刺客的夥伴——海瑟姆手持袖劍,擁有艾吉奧·奧迪托雷的魅力,並透過解放原住民與羞辱英軍士兵扮演英雄角色。震撼的真相在他說出聖殿騎士信條時揭曉:「願理解之父指引我們。」突然間,我們意識到自己一直在協助該系列的宿敵。
這精湛的轉折完美體現了《刺客教條》的巔峰表現。雖然初代遊戲引入了引人入勝的「獵殺目標」概念,但其角色缺乏深度。《刺客教條2》透過令人難忘的艾吉奧有所改善,但切薩雷·波吉亞等反派仍塑造不足。直到《刺客教條3》,育碧才對獵人與獵物同等用心,達成了後續作品難以企及的敘事與遊戲性和諧境界。

儘管RPG時期的作品獲得評論界讚譽,許多人認為該系列已衰退多年。原因眾說紛紜:有人批評對抗神祇的神話戰鬥,有人反對歷史人物取代虛構主角。但核心問題更深層——在膨脹的開放世界下,角色驅動的敘事逐漸流失。
系列轉向RPG機制——對話樹、經驗值系統、微交易——創造了龐大卻空洞的體驗。支線內容感覺重複,主線故事也缺乏早期作品的細膩。《奧德賽》等遊戲或許提供比《刺客教條2》更多內容,但大多顯得造作且缺乏說服力。
玩家選擇理論上能增強沉浸感,卻常適得其反。大量分支對話導致文本精緻度不如早期緊密編排的敘事。動作冒險時期的聚焦手法,讓細膩角色不必遷就玩家每項突發奇想。
《奧德賽》內容常顯生硬——當NPC明顯表現得像程式實體而非真實人物時,沉浸感便遭破壞。這與PS3時代精湛文本形成鮮明對比:無論是艾吉奧激昂的演說,或海瑟姆對兒子康納最後的殘酷話語——
「別以為我會哭泣認錯。我早該殺了你。」

近代作品也簡化了刺客與聖殿騎士的衝突。早期遊戲探索道德灰色地帶——《刺客教條3》垂死的聖殿騎士迫使康納質疑使命;威廉·詹森聲稱聖殿騎士能阻止原住民滅絕;湯瑪斯·希基嘲諷刺客的理想主義;班傑明·丘奇將衝突歸為「觀點」問題。海瑟姆甚至動搖康納對華盛頓的信任,揭露這位將軍下令焚燒他的村莊——讓玩家質疑一切。
《艾吉奧之家》旋律的歷久不衰正反映此差異——它捕捉的是個人悲劇,而非僅是歷史背景。當今遊戲擁有驚人規模與畫面,但我希望育碧能重拾定義系列巔峰的聚焦敘事。遺憾的是,在遊戲產業沉迷於無盡內容與服務型元素的現狀下,這般深刻的敘事可能已不具商業可行性。
最新新聞
更多 >-

- 愛死機器人第四部:覺醒玩具與恐龍寶寶的相遇
- Dec 14,2025
-

- 野蠻人柯南於真人快打1的實機畫面正式公開
- Dec 13,2025
-
- 星際大戰:俠盜降臨任天堂 Switch 2
- Dec 13,2025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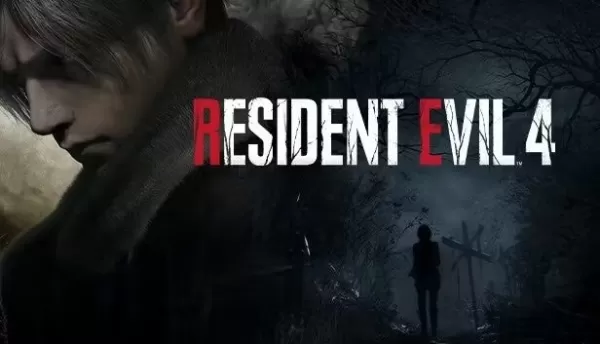
- CAPCOM 特賣:《惡靈古堡4 重製版》與《龍族教義2》限時優惠登場
- Dec 12,2025
-

- 索尼 WH-1000XM6 降噪耳機 現已正式開售
- Dec 12,2025